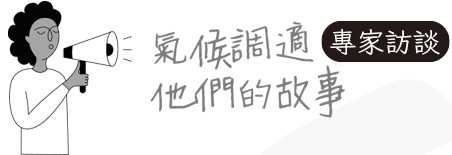知識服務 / 知識專欄
【氣候調適。他們的故事】黃品涵:跨越世代的氣候調適工作,源自於「愛」的理由
發表日期:2025-05-13 作者:陳玲瑤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專案佐理研究員
.png)
.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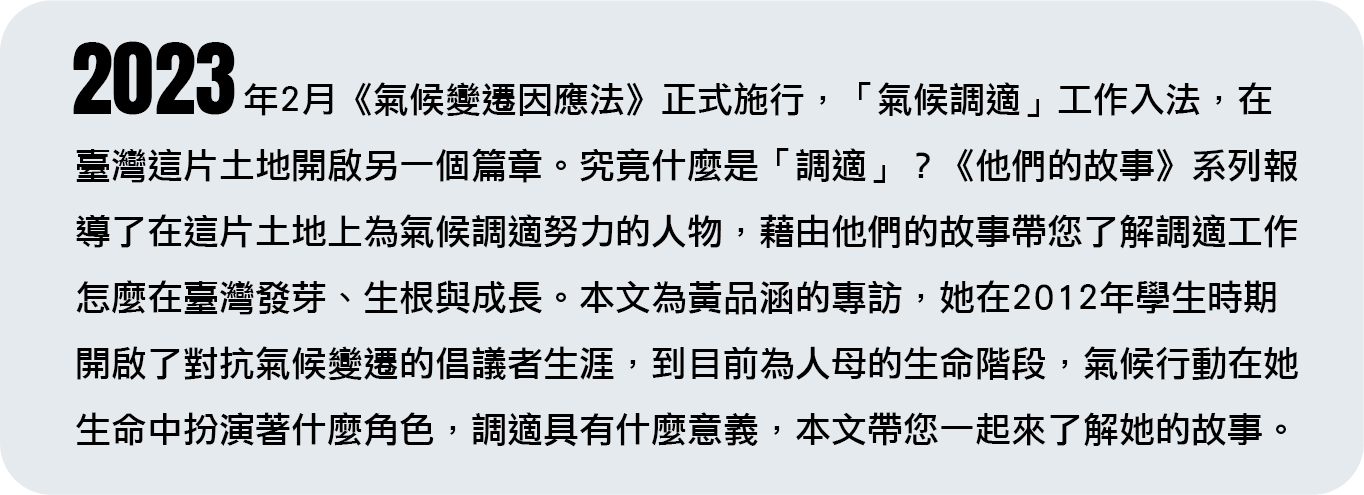
2024年的盛夏,剛生產完6天就出月子中心前往總統府參加「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的黃品涵笑笑地說:「我不敢讓我媽知道,她會覺得才剛生產完6天就出去吹風…但我還是去了,因為我大部分的生命歷程都在參與氣候變遷相關的議題,必須把握每一個機會,更不可能再浪費每一天、每一年…我確實也感覺有了孩子之後,使命感與迫切感都更強烈了…」
.png)
黃品涵,七年級後段班,從2012年研究所時期開始關注氣候變遷議題,角色的轉換從臺灣青年氣候聯盟理事長、智庫研究員、參與《氣候變遷因應法》修訂的立院法案助理,到目前的民間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她氣候政策倡議生涯已來到了13個年頭。而臺灣在近10幾年也開始逐漸感受到氣候變遷的威力:逐年破紀錄的夏季高溫、水資源議題擺盪在旱澇的極端事件之間,國際上則面臨供應鏈減碳的趨勢不得不提早佈局。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為臺灣帶來的各種挑戰,2024年6月賴清德總統宣布設置「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並親自擔任召集人,邀請了產官學研代表為國家氣候治理方針與氣候變遷韌性建構提出建言,使委員會成為社會溝通的平台之一。黃品涵在入夏前接到總統府的邀請,希望她能成為「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的民間委員。
.png)
「我就跟他們說那時候我可能去生了喔!」 黃品涵回憶起第一次對策委員會開會日期是7月25號,但她的預產期是8月2號,不料強烈颱風凱米在7月23至26號侵襲臺灣,第一次的會議就延期到8月8號。「我的孩子非常準時在8月2號預產期出生了,但委員會沒有代理制,無法到場的話只能請假...」黃品涵認為氣候行動的主要量能之一來自民間,包含公民團體、學術與產業界,民間委員在委員會裡面展現的意志以及相關的意見都是很重要的,尤其第一個會議代表啟動,而討論的第一議案是氣候調適,她毫無懸念地做了決定:「會議請假是可以提供書面意見,但我覺得還是有差,所以我決定要去,但是不敢讓(我)媽媽知道我出月子中心,吹風這件事。」
氣候調適為什麼重要?我們現在做的事是調適嗎?
因為人為排放溫室氣體而造成全球持續升溫與極端天氣事件更頻繁發生的趨勢,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是目前因應氣候變遷的兩大策略。而調適相較於減緩是大眾比較不熟悉的觀念。減緩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減低讓地球升溫的來源,減碳目標也相對清楚,例如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於2015年宣示努力將全球減緩目標設定為控制地球升溫幅度不超過1.5℃,以及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2050年的淨零排放目標。然而調適的內涵就需要較多的解釋,來協助大眾與相關制定、執行單位理解。目前氣候變遷已造成全球各地天氣災害與極端事件發生得越來越頻繁,未來的氣候風險預期會隨著暖化程度越高而提升,而調適就是致力於治理現在與未來的氣候衝擊和風險,以減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負面影響。
 調適就是致力於治理現在與未來的氣候衝擊和風險,以減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負面影響
調適就是致力於治理現在與未來的氣候衝擊和風險,以減少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負面影響
黃品涵提到在討論《氣候變遷因應法》調適專章的過程中,常常會聽到類似的疑問:「我們現在做的事不就是調適了嗎?氣候變遷很嚴重,我們已經在調整了啊?」 的確,中文「調適」的意思是面對改變或影響時做調整,但在討論氣候變遷治理的脈絡下,「時間尺度」就是一個關鍵的考量要素。現在大部分既有的防減災計畫對於歷史災害經驗已有相對周全的準備與到位的相關措施法規,不過面對未來的氣候風險則需要氣候變遷科學推估資訊來支援未來風險的評估與調適規劃。除了「時間尺度」需要拉長考量,另一個調適的核心觀念為「因地制宜」,因為每個地區受到的氣候衝擊與未來的風險程度皆不相同,攸關當地的氣候災害類型、社會經濟資源以及如何因應的策略。
以去(2024)年7月凱米颱風對高雄帶來的淹水災情為例,極端降雨又適逢臺灣年度大潮,20幾年來高雄建設的25座滯洪池容納了近500萬噸的洪水,黃品涵說道:「面對極端降雨事件時那些滯洪池都有裝滿,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平時很少人知道它們拿來做什麼」,不過因為凱米帶來的極端降雨超出了原本的防洪設計,再加上年度大潮現象,部分高雄市區仍然經歷淹水災情,她強調:「如果能透過未來氣候變遷風險分析去辨識出極端事件發生強度與頻率變化,在災害事件發生前去做相對應的承洪與土地利用等調適規劃,打造淹水韌性,比災害發生後再啟動因應方案理想很多。」過往颱風災害經驗使得臺灣防減災做得很好,不過面對氣候變遷升高了災害風險,她推了眼鏡,語氣堅定地說:「調適工作啟動的時間點就需要再往前挪動,準備時間再拉長,搭配最新的氣候變遷推估資訊來評估短中長期的氣候風險,不斷地滾動地檢視調適方案來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調適的工作未雨綢繆,而且氣候變遷帶來的長期、大規模影響,讓調適工作勢必得考量20、30年以上的氣候風險,預作政策與資源的相關準備。
調適工作吃力不討好?
「調適觀念的溝通跟執行面的確會遇到不少困難,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超越政治任期,如果政治人物任期內沒發生什麼重大災害或損失,就看不到調適的效益,無法成為政績,是一件做了但不見得會得到稱讚的事。不過我覺得溝通這件事會變得越來越容易。」黃品涵略帶無奈地舉例說明:氣候變遷改變降雨頻率進而導致更乾燥的環境,釀成了今年 (2025年1月)發生在美國洛杉磯的驚人野火燒毀了好萊塢富人豪宅區的新聞, 以及臺灣每年破夏季高溫紀錄的趨勢,讓各地民眾驚覺極端事件不再少見,氣候變遷的影響已經體現在日常生活中。「跟10年前比,現在來溝通氣候調適變得相對容易,這背後很悲傷的原因就是氣候變遷趨勢目前難以逆轉,它帶來的影響跟衝擊已經越來越嚴重了。」她語氣變得略低:「我確實也感覺有了孩子之後,使命感與迫切感都更強烈了,你會思考:我要留給孩子什麼樣的未來?」

跨世代的調適議題
氣候變遷的影響跨越人類數個世代,同時應對策略與執行方案也必須由不同世代來承擔。黃品涵提到:「我真的覺得我們中年這一輩的人無法迴避減碳的工作,接下來20年勢必得做,但是調適是現在青年跟未來世代一定會碰觸的挑戰,現在必須有更多資源進到調適,因為調適作為直接影響他們的生命、財產、健康,我們的責任應該是讓青年跟未來世代認知到這件事。」
她觀察到在臺灣的年輕世代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看法呈現兩極反應,與世界趨勢大致吻合:「跟我們青年氣候聯盟接觸的年輕人在理解調適上是快速的,會感覺和他們切身相關。把時間的尺度拉出來,5年後、10年後她/他才幾歲,20年後的氣候跟生存環境變得如何? 例如要買房該買在哪裡? 想到這些就會很有感。」有些年輕人很積極參與氣候行動,投身相關領域去產生影響力,不過也有些年輕人會覺得不管做什麼都沒有用,短視一點,躺平就好。
「我已經快變成中年了」黃品涵訕笑但堅定地說:「我們中年跟壯年世代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一些減碳、調適基礎工作建立起來,不讓青年跟未來世代覺得一點希望都沒有,當這種態度變成一種風氣的時候,會讓整個氣候行動變得很悲觀。」

臺灣的氣候調適元年
在民間團體、學界與各方人馬努力、協調下立法院於2023年1月10日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除了將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碳費正式開徵,並新增調適專章,強調國家調適規劃須以氣候變遷科學為基礎,檢視現況與未來可能面臨的氣候變遷風險,以增進相關環境、災害、設施、能源調適能力,提升臺灣整體氣候韌性。而《氣候變遷因應法》於當年2月施行後,中央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以及地方政府的「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都陸續提出與核定。黃品涵表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有了大方向,中央跟地方都需要依法進行調適規劃和執行,也代表需要更多資源、人力的投入。」
她還提及臺灣的調適政策發展其實很早就啟動了:「2012年經建會時期提出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以及後續推動了中央部會8大領域的行動方案,我對調適議題的啟蒙也就是發生在2013年左右,參與學校老師執行的國科會調適相關計畫。政治的意志與動能可以從上而下滾動氣候行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軸線、力量與資源。」
讓愛傳下去
跨世代的調適工作從民間出發
除了中央、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角色,民間的力量持續累積也至關重要,黃品涵提及:「提升民眾的氣候變遷風險意識,不管是淹水、高溫、健康、生計影響,溝通都需要時間,但如果慢慢累積,公民社會動能帶來的效果是最長遠的,這也是我在立法院那邊工作告一段落來到民間團體-媽盟的重要目的。」
接下來黃品涵除了繼續參與總統府召開的「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以民間委員的身分繼續將公民社會的聲音帶進去中央,她所屬的民間團體「媽媽氣候行動聯盟」也將致力於地方調適培力工作,讓越來越多民眾了解「氣候調適」的內涵,以及科學資料如何與在地生活、災害經驗對話,讓調適接地氣。
訪問到了最後,筆者問及:「那黃媽媽知道妳生產完6天後就出去開會吹風這件事,她怎麼說?」黃品涵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我在總統府開會期間她還打來5、6通電話找我。那一天是8月8號,我稍晚有打給爸爸跟他說父親節快樂,也跟他提到去開會但沒跟媽媽說的事。後來,有次我回爸媽的住處用電腦,發現爸爸把8月8號開會那天的照片跟新聞報導都保存了下來。」至於黃媽媽到現在是否知道她出門吹風這件事,可能只有黃媽媽才知道答案。
黃品涵認為氣候調適有三個特點
【氣候調適。他們的故事】系列
延伸閱讀